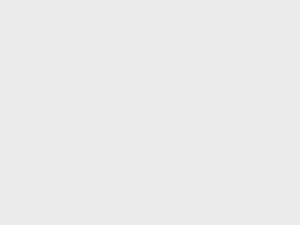- A+
有些念头宛若夏末的卷云,无法久待,绝美或凄凉,心头一阵起伏,秋雨一来,散了就散了。树影子细碎纷乱的投影。河边参差青碧的水线。飞鸟长空的悠呜。窗玻璃上的倒影。萤火的明灭。来路不明的旋律。错过了的阵雨。诸如此类,一闪而过的念头。
夏日的尾声一切都宛若一闪而过的念头,某个曾经的空缺已经如同蝉声那样辽阔不可测,不会再有谁在花丛里踱步,也不会再有黄金猎犬在草地上长长的奔跑,不会再有人吹口哨,他们转往林子里去了,在那里有更多的果实和落叶,更适于缓缓的张望,更适于在风中梳理蜷曲的毛发,并且放下伪装。
已经放手的风筝将继续悬挂在树梢,已经漂走的缎带将继续伪装成水草,黄昏的雨不会再扰乱谁的思路,不会了。
然后念头总是留不住,今天想起来,明天就躲在风景,仿佛看见它,又仿佛只是幻影。什么也记不住,可是又明明知道有什么被忘记了。
不知道忘了什么。这是一种不彻底的遗忘。像是哪里来的灰印子,拂不掉。
于是我开始记忆的练习:记住那条桥和白鹭鸶的关系。记住这双鞋和红砖道的关系。记住那一棵柚子树。记得这个风的感觉。记得丝瓜藤的须和篱笆。记那猫的神色。那狗的姿态。这盏灯。那壶茶。
然后它们就如同生命中的时时刻刻,如水一般轻柔婉转地往四面八方流逝了。更久远的细节有时候会像黎明前的梦那样静静浮现,有时候不会。一闪而过的念头有时候是从时间之流浮上来的,它们像沉在深海的船骸,总要过了很多年,才会重新被你忆起。
我不太记得,第一次因为高兴所以买一瓶红酒自己慢慢儿喝是哪一年了,也不记得那酒是醇是涩。不记得第一次因为感动于瓷器的美而买的茶杯是哪一只,不记得第一条桌巾和第一套椅垫,不记得第一次唱到昂贵的红茶是几岁,不记得第一次尝到精纯的巧克力是在何处,不记得第一次在雪里滑倒是在哪个街角,我也忘了从何时开始,我渐渐知道这些小事的意义而且试着记得它们。
我还记得的是,第一次觉得红酒好喝大概是一九九六年份的加州纳帕山谷苏维酿。念念不忘非常想买但始终没买的白瓷杯是柳宗理的设计。我非常喜欢的桌巾是一幅手工白色的爱尔兰风蕾丝钩针。昂贵的红茶也许是在纽约喝的。精纯的巧克力,大概是在日本朋友家里吃过的最令人难忘。在雪里滑倒其实很痛。
我想当时的我必定也是千方百计告诉自己要记得,结果还是忘了,还是让它们沉下去了。也许多年后的哪一天它们又会浮上来,又会在散步的时候乱了步伐,在秋雨里散得宛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