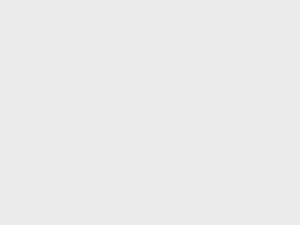- A+
在父亲去世的两年前,他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故作轻松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说的是他死了以后。他说:“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或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选一些发表。”
说这话时是在我的书房里,父亲想找个地方放下箱子,就像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赶紧卸下去的人一样。最后,他悄悄把它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父亲走后,我围着那个箱子转了几天,却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承载我的童年及过去的记忆。可现在我却不能碰它一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其中沉重的内涵。
上世纪40年代,父亲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他还把瓦雷里(法国诗人)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他不想过那种在一个穷地方写几首没人看的诗的生活,于是放弃了他的作家梦。
可真正让我无法打开父亲箱子的第一条,就是我害怕发现父亲是个优秀作家。因为如果从父亲的箱子里拿出来的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就必须面对父亲身体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这个可能性太可怕了。因为即便是一把年纪了,我也只希望父亲就是父亲,而不是作家什么的。
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男人或是女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烟,还时不时站起来,望着窗外在大街上嬉戏的儿童,如果幸运的话,可能还能看到绿树或其他风景,又或许他只能面对一堵灰墙。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箱子,还因为父亲没选择和我一样的生活而生气。但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妒忌”。每逢想到这点,我就会轻蔑、恼怒地大声问自己: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孤独地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吗?或是与芸芸众生一起,过着或装出过着舒适生活的样子?这些问题实在太让人烦恼了。谁说幸福是衡量生活的惟一标准?大众,报纸,每个人都把幸福当作评判生活的重要尺度,这件事本身是不是说明其反面也很值得探寻一番?
我第一次打开父亲的箱子时,就是受这种情绪影响的。父亲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情的秘密或是不幸,而他又只能默默忍受,倾泻在纸上?一打开箱子,我就认出了其中的几本笔记,它们大多是父亲到巴黎去时写的。我就像读我所崇拜的作家的手记一样,急切地想要了解父亲在我那个年纪都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不久后我就意识到不是那么一回事。最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在笔记中时不时能读到作家的腔调,一点都不真实。在对父亲写作时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担心之下,我开始担心内心深处的自己是否也不真实。
当我关上父亲的箱子时,被放逐感和对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怀疑感就深深地包围着我。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多年来它们就一直在我的阅读、写作当中存在着,我也一直在研究甚至深化着这些既让人精神崩溃,又让人情绪高涨的情感和色彩。只有当我写书时,我才对真实性的问题(比如《我的名字是红》和《黑书》)和边缘性的生活(比如《雪》和《伊斯坦布尔》)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
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但是从父亲的箱子和伊斯坦布尔人苍白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而且离我们很遥远。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情绪,有些人可能还遭受着更为深刻的物质匮乏,没有安全感和受堕落感折磨。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还是土地缺乏、无家可归和饥饿……但今天的电视和报纸可以比文学更为迅速简洁地报道这些基本问题。而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性的耻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和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的担心……不论何时当我看到这些被以夸张的语言表达出来时,我就知道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深处的黑暗。我们曾看过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常常因为被恐惧折磨得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财富,对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有着不一般的自豪,但他们时不时的也由于自我满足,干出一些同样愚蠢的事来。
而促使我们闭门数十年写作的则是一个与之相反的信念。那信念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文字会被读到并被理解,因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人都是相似的。可这似乎有点过于乐观了,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对被挤在边缘,被排斥在世界外围的怒气留下的伤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对西方爱恨交织——现在我也多少体会到了,这是因为我和这位伟大的作家一起经历了对西方的爱恨情仇,一起关注了那在另一方向上建立的另一个世界。
看着那箱子,我觉得父亲在他写作的那些年里,可能也发现了这些乐趣:我不应该对他预先判断。我必须用一颗容忍的心来阅读它——看看他在旅馆房间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在把箱子留在我办公室后一个星期,父亲又来看过我一次,我们聊了些琐事。后来他终于看到箱子被我挪动过了。我们就互相看了看,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我没说我打开了箱子,我只是把视线移开了。他立刻明白了。就像我明白他明白了一样。所有的明白就在几秒钟之内明白了。父亲是一个快乐、懒散但却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他只是照例冲我笑了笑。
在父亲把箱子交给我的23年前,就是我22岁时,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说《杰夫德贝伊与其子》。我用颤抖的手将打印稿拿给父亲看,想听一点他的意见。这并不仅是因为我相信他的品位和智慧,以及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因为他并不反对我成为一个作家。我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消息。两个星期后他来了,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拥抱,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非常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他告诉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赢得像站在这里接受这个奖项这样的无限快乐。
父亲在2002年12月去世了。
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给予我这无上光荣的奖项的瑞典文学院的同事们和尊敬的来宾们面前,我深切地希望此刻他就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