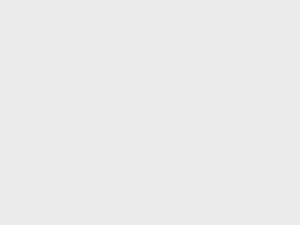- A+
我的父母,詹姆斯·布勒斯南和玛丽·麦克瑞,是高中时代的恋人。当我降生的时候,他们早已清楚曾经梦想的幸福生活结束了。两年前,妈妈随爸爸从
战场归来,带回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哥哥吉米。吉米在部队医院出生,难产造成他的脑部缺氧。那个时候还没有医学手段能够检测他的病情将如何发展
,渐渐地爸妈才发现吉米的脑部受损程度有多严重。
孩提时代,我已觉察到爸妈的悲痛。吉米总是不断地发问,我可以做果冻吗?我的帽子在哪儿?奶奶什么时候会来?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明白自己该做
些什么,他总是向往着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并且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来抱怨。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份礼物,它拯救了我们。
妈妈希望我们的生活围绕吉米打转,因此她变成了狂躁的玛莎·斯图尔特(美国家政女皇),脾气本来就很温和的爸爸则变成了一个圣徒。我也被卷入
哥的生活中 ——充当他的保护者,爸妈的后盾。小时候,我从不拒绝妈妈让我带哥哥出去玩的命令,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我明白她的意思:如果你想
要我陪,就得带上哥哥)。我试着引导哥哥做一些他能胜任的脑力游戏,比如捉迷藏,而避免那些他不能做的游戏,比如玩玻璃珠和挑竹签。
我们从来没有把吉米一个人落下,我们也不去他不能去的地方,比如电影院、博物馆和戏院。于是,我邀请邻居的孩子们来我家玩。他们很喜欢我家,
不仅因为那些可口的零食和冰激凌,他们喜欢我家的气氛,完全是小孩子的天地。
爸妈负责家里的所有事。早上,妈妈教吉米一些实用的技能:刷牙(成功),系领带(失败),把皮带穿在裤腰上(成功了一半——前面他会穿,后面
不会)。我负责巡逻吉米的活动领域,并维持正义。我开始讨厌那些欺负弱小的人,我发现没人注意时,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常常干坏事。欺负哥哥的
不是那个有哮喘病脸色苍白的男孩,而是那个拥有斯奇文牌三速自行车和特德威廉棒球棍的高大英俊的小子。
那时,我把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列入黑名单。我像瘦小的扎着马尾的迈克·华伦斯(美国著名的新闻调查记者),追踪那些没有公正立场,偏袒自己孩子
的父母。折断吉米的自行车训练轮子是那帮家伙的一个小把戏。一气之下,我跑到帕特克家告诉他爸他的儿子是那帮捣蛋分子的头儿。他爸瞪了我一眼,在
叫他太太下楼来的同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太太从没出现过。第二次,我朝他家扔了一块石头,还把帕特克的鼻子打出了血。很多年后,我的儿女发现
我儿时的成绩单,令她好笑的是,我的仪表课只得了“F”,玛丽塔·约塞夫修女还写了一句评语,要我把草率的处决权转给他。
牧羊人学校的修女们似乎想把我们每个人都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学得很快,每个人都有正常的思维,修女们尽有可能让每个孩子都接受教育,但
对于吉米还是无能为力。那爸妈该做些什么呢?肯尼迪家族是个很好的参考例子,他们的情况表明:即使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金钱和专家,有时也无济于事。
肯尼迪的大女儿露斯玛丽(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大姐),出生时脑部缺氧,肯尼迪为此伤心不已;他给他做了脑部手术并把她送到威斯康星州一个特殊的小
镇,没有这样的学校。如果要去远离我们的地方上学,哥哥是不会同意的.
然而,他去了一家生产锅柄和船索的残疾人工厂。虽然产品在当地市场饱和,工厂还是雇用了哥哥。起初,吉米四处张望,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没有残疾”,他喃喃自语,但他很快习惯了那里。晚餐时,他跟我们详细描述当天的工作,实际上他的每一天都是相同的,这也是他喜欢在那儿工作的原
因。他的每句话都让我们兴奋不已。
再后来,吉米去了梅卡尼克斯堡的海军仓库,爸爸在那儿为他找了份搬不同颜色的纸箱的工作。他不时被人欺负,还学会了妈妈从没教过他的脏话,但
他的老板洛德哈格很照顾他。他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远远超出我们的期望,比他在第一家工厂做编织活好得多。吉米受到了奖励,不仅因为他从没请过一天
病假,还因为他发现了更有效地搬卸纸箱的方法。每次听到人们抱怨超市给残疾人预留太多的停车位时,我就想告诉他们吉米的故事。
吉米长大后,与爸爸的关系更为亲密。每天早上他们一起吃早餐,准备好午餐饭盒,再开车去上班。1991年,爸爸在一声高尔夫球赛后跌倒,旋即去
世,吉米的世界垮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带着啤酒冰镇器和俱乐部成员走出房子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爸爸走后的一周里,吉米没掉过一滴眼泪,直到一些
记忆碎片开始在他脆弱的脑海里浮现。
我请了一个人和吉米同住并开车送他去上班,我努力想让一切回到从前,纵使吉米自己也意识到他曾经熟悉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问他:“你想念爸爸
吗?”他说:“玛格丽特,你不知道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6个月后妈妈死于肺癌。父母过世,孩子们都很伤心,我则陷入了恐慌。那时候我离婚了,我的女儿康妮刚搬走开始她的新生活,我的弟弟埃德蒙刚结
婚。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照顾吉米了。
从那以后,我渐渐明白,我对吉米的照顾永远没有尽头,但没有必要恐慌。吉米还没适应不能和爸爸一起去上班的日子,于是他来到华盛顿和我住了一
段时间。起初,吉米总是跟着我外出,他从没独自呆过。一天早上,他穿上参加丧葬的礼服和我去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参加总统候选人的早餐记者招待会。坐
在吉米旁边的记者问他:“你和谁在一起?”
“我的妹妹。”吉米说。
“你的妹妹和谁在一起?”
“她和我在一起。”吉米疑惑地答道。侍者端来橙汁和咖啡,记者招待会只供应这个。吉米想要一些蓝莓蛋糕,侍者满足了他的要求。
渐渐地我设法让吉米更多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想回梅卡尼克斯堡的海军仓库工作,住在爸妈的房子里。于是他又在那里工作了11年,照顾他的人也换了
很多个。他现在对邻居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你的草地上有落叶吗?吉米有清扫的工具;你有邮件要取吗?吉米可以帮你。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妈妈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当然,如果妈妈没有把吉米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根本就无法生活。建立一个包容吉米缺陷的
家庭是可能的,吉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充实。
世贸中心惨剧发生后的几天,我对此有了清楚的认识。9月16日,吉米来华盛顿和我一起庆祝他57岁生日,因为“9·11事件”造成的混乱,我们家人没
能聚在一起。于是我叫来朋友帮忙准备生日庆典,尽管他们因不停工作已经疲惫不堪。我顾不上礼仪,大叫:“请带礼物!”
吉米安排菜单:用妈妈的面团做的比萨,德国巧克力蛋糕和冰激凌。客人是吉米这些年交的朋友,他们带来了理想的礼物:微波炉爆米花、龟牌车蜡、
乡村音乐 CD、衬衫,还有很多让健康饮食专家头疼的饼干、薯片和花生。想想这周美国遭受的打击,我们深情地吟唱生日颂歌好像演唱那首伟大的赞美歌
曲《美丽的亚美利加》。
第二天早餐时,哥哥递你我一沓白色信封,说:“这什么不打开看看?”头天晚上他很安静,以致我忘了,如果不和客人交谈,他不知道哪张贺卡是属
于哪份礼物的。我读每张卡片时,他都点头,好像卡片上那些深情的话语正是为他写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如此。吉米给了我的朋友们在经历这场灾难后一个表达他们真挚情感的机会。他提醒我们,亲情和友情可以鼓励每个人,如果你
曾经需要它。那些生日贺卡放在他的卧室的梳妆台上,那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年幼的时候我不曾意识到,爸妈早已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永久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