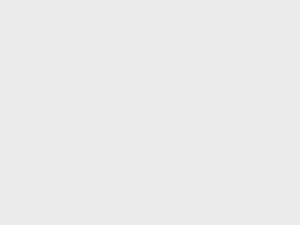- A+
代序
关于黄昱宁,随便说说
潘向黎
在我的印象中,黄昱宁一向是个稳当的女孩子,不会有什么让人跌破眼镜的举动。但是她这回让我有点惊奇。不是因为她要出第一本书,而是因为她居然让我给她作序。我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如何有资格做这样德高望重的事情,况且我和她的交情也只是淡如水,要介绍她有的是比我合适的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看重我,肯定是她难得一见的情绪化的错误吧。但她也算我的作者,又经常收到她送的翻译小说,这个时候出来喝一声彩也是应该的,也就不推托了。
黄昱宁写的东西,我在各处看了不少。端的是满腹经纶的样子,不象她的同龄人,一般多是靠感觉,莺燕桃李一大片,好看是好看,缺点只有一个:不看也不会损失什么。有的还无端有一种“代”的优越感,目空一切,有一股子戾气。
黄昱宁不但书读得多,而且中西合璧。在她心里,黑塞、伍尔夫和苏东坡一样亲近;在她笔下,西方的前卫妖冶和东方的古典中庸亲密无间地熔为一炉。正如她用宋词“当年拼却醉颜红”来写梦露——亏她想得出来。这个味道写来不易,难为她小小年纪怎么就有这个悟性和道行。其实这两者之间本来是有一堵墙的,有的人是在墙上跳来跳去,自己觉得学贯中西,旁人看着只觉得累,可是黄昱宁虽然不能说推倒了墙,但是穿越自如,好像没有墙。这个小女子,功力不能小看。
我的正职是在报社上班,第一次发表她的随笔的时候,给她打了电话,说她写得很好,叫她多写。这话她记到了今天,她可能以为我在提携她,其实是她这样有生气的文字给我们暮气沉沉的版面带来了清新。遇到这样的作者,对编辑苦恼的生涯是一种安慰。我真恨不得天天有人让我打这样的电话,说这样的话,但是啊但是,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容易遇上的。
其实我当时对她的评价是背着她说的:黄昱宁的内功扎实,招招都是少林武当,不管是写哪一路,她都可以一直写下去。许多只会剑走偏锋的人,玩感觉玩到头了,就玩完了,可是黄昱宁可以不紧不慢地写下去,后劲足。
有时候猜测黄昱宁是个怎样的人。好像是个清醒的人,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如何去做到,不紧不慢,有板有眼。她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书也翻译了那么多本,当编辑也编了那么多好书,好像单位里还有个官职,随笔也写了那么多,作为这个年龄的人,她应该算很主流很丰收了。甚至连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事,她都是在最应该做的年龄完成,不像有的人,写一点劳什子东西,就觉得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一定要牺牲常人正常的生活,那般糊涂油蒙了心让文字荼毒了人,黄昱宁是不会的。自恋或者颓废,好像也不属于她。她似乎早早看透了生活的真相,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和胸怀。我相信她是个冰雪聪明的人,因为聪明,所以不太做白日梦;因为聪明,所以和生活握手言欢。
黄昱宁是自信的,因为她通过书本、电影里的人,已经活了好几辈子。在她的作品中,你会觉得她如此富有人生经验,如此洞察世态人心,简直老辣,又不失分寸感。只在偶尔的字里行间,你会发现女孩子精致的淘气,灵光一闪。那个时候,让人忍不住微微一笑。
二○○三年十一月
------------
作者简介
------------
黄昱宁,一九七五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播专业。现任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发表译着近百万字,其中包括小说《庭院中的女人》、《撞上门的女人》和传记《狂恋大提琴》等。杂文、随笔刊于《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文学》等。
Email: [email protected]
------------
遭遇巧克力的诱惑(1)
------------
朱莉娅·比诺什那张曾经在《布拉格之恋》、《蓝》、《英国病人》里冷得慑人的脸浮在《情迷巧克力》的电影海报上——脸还是一样的脸,表情却经过了新的铺排:发梢微挑,眉头稍扬,嘴角略展,一束高光聚在伊的眸子里,如是,竟塑成了一个别样的比诺什。我先想起英文词vivacious,再踌躇着斟酌它的译法——妩媚,明妍,鲜活,灵动,都有些意思了,却又都像是少了点什么。
左侧是约翰尼·戴普的半张脸。比《剪刀手爱德华》那会儿,是不可救药地见老了,但棱角里散逸的柔情依然似水般糯软。男女主角的视线被比诺什手里的宝贝牵引在一起,款款地打了个结——那是一枚巧克力,带乳色的螺旋纹,多半还嵌着榛仁葡萄干什么的,看得人舌尖一阵酥麻。
电影海报上这一刻的灿烂也给搬到了原小说的封面上,腰封上的广告语说,这是一本能读能尝更能回味的好书。
这话真的不算夸张。翻开书页,触目皆是这些足以全方位调动我感官的句子:
“……上唇碰到硬硬的巧克力海贝的外壳,里面包着软软的脱肥……每一层的风味都不同,如同香味纯正的葡萄酒,有点苦涩,又有点研磨咖啡的馥郁;口腔的温度又令香味复活了。它灌满了我整个鼻腔。这位味觉的女妖让我哭泣呻吟……”
仿佛有某种狂欢的节奏和旋律于静谧处奏响,倏然间,我听见了自己的味蕾徐徐舒展开的声音。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中叶的法国,一座时间似乎凝止在中世纪的闭塞小镇。在这个人口只有二百多的地方,民风淳朴到呆滞,秩序井然到压抑,生活的调色板上是一味恬淡而空洞的灰。没有生趣的灰。
二月里夹杂着热烘烘油腻腻香味的风带来了维亚纳——一个眼里的神采和背后的故事都让人捉摸不透的未婚妈妈。她把可可豆的浓褐,杏仁的浅黄,牛奶的纯白,糖霜、果脯的斑斓五彩,统统堆砌在新开的“美味糖衣杏仁巧克力铺”的橱窗里。整个小镇为之晕眩。人们半是猜疑半是兴奋地想,多半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要发生了。
对于巧克力铺对面教堂里的雷诺神父而言,维亚纳的到来又岂止是让他晕眩?瞧她都干了些什么:鼓励约瑟芬背弃无爱的婚姻,离家出走;怂恿恶疾缠身的阿尔芒德不再苦苦节食,以放弃治疗来换取生命中最后的享乐;与那个不修边幅的吉卜赛人鲁互通款曲,居然打算在复活节办什么“巧克力节”——上帝啊,这不是在向教会的权威挑战吗?如果她不是一个yin邪的女巫,又怎能洞悉每个顾客的烦恼,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最合乎他们口味的巧克力糖来“对症下药”,一步步诱导无知的羔羊们滑入纵欲的泥淖?
雷诺神父一天比一天焦躁、惶惑,继而愤怒、癫狂。在巧克力节的前夜,他潜入维亚纳的铺子,想把橱窗里陈列的美味一一摧毁,然而,然而……
巧克力的香味虽在意料之中,依然令人震惊。有那么一会儿工夫,那股香味成了黑暗本身,犹如一层浓郁的褐色粉末,窒息了神父的思维。好歹尝一块吧,他想,就一块。
欲望之门一经开启,便再也没有了关上的可能。一切恍然如梦:雷诺神父疯狂地大快朵颐,在巧克力中忘乎所以地打滚,他想像着自己置身于巧克力的田野里,躺在巧克力的海滩上,摊手摊脚地晒太阳。
我想,每个看过电影《情迷巧克力》的人都不可能忘却这一幕,画面的戏剧感和冲击力强烈得让你震颤。不过回过头来再读小说,却发现文字所能延伸的空间自有影像所无法企及的深度。文字一行行映入眼帘,分明是静默的,但耳边却有鼓点响起来,是那种特别简单特别强劲的节奏: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快乐它没有什么道理。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想起儿时,巧克力何尝不是每个孩子最简单最直接的快乐源泉?包在银纸里的香草巧克力,分成那么小的长方格子,总是小心翼翼地盘算好一天吃一块的,临到睡前又忍不住蹑手蹑脚地起来,给齿颊和味蕾预支了明天的份额,这才带着满嘴淡淡的苦味入梦去。恋恋不舍地吃完一盒动物巧克力,舌尖上来不及褪去的喜悦又从心底里升起——因为留下的那个铁皮盒子是可以搁文具的。从此,课堂上又多了一个打发寂寞的办法——借着拿一支铅笔取一块橡皮,便可以在想象中重温芬芳之旅。那种妙不可言的乐趣,是别人分享不来的呀。
长大了喜欢看费列罗金莎巧克力的广告:就那么一张淡金色的包装纸,如同一片不甘坠落的秋叶,伴着女中音飘飘渺渺的解说词,缓缓飞过整个房间。诱惑就沿着滑行的轨迹朝你扑面而来。
但是彼时的快乐已不复孩童样的单纯。与巧克力的芬芳一同闯入脑海的是卡路里对照表上触目惊心的数字,是磅秤上令人沮丧的指针。最要命的是,我们都有类似雷诺神父的那种可怕的体验——只要吃上一块巧克力,就会忍不住吃第二块,然后是第三块、第四块……最后的最后,便是一波接一波“才下舌头,又上心头”的负罪感。
------------
遭遇巧克力的诱惑(2)
------------
所以美国的《出版家周刊》会把《情迷巧克力》看成是一个“有关内疚的故事”。说来有趣,人类是一种最容易为自己的快乐内疚的动物。你总忍不住要担心快乐背后藏着温柔的陷阱,当蓬蓬勃勃的生命力从某个地方喷薄而出的时候,第一个被吓倒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于是就有了压抑与反压抑周而复始的较量,如同弹簧般将人性的张扬舒展到最高点。美食如是,爱情亦如是。
当然有爱情。在芬芳四溢的巧克力词典里,这永远是一个核心字眼。据说,巧克力的主要成分之一苯基胺能引起人体荷尔蒙的某些微妙的变化,能让人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就像一场仲夏的热恋。
巧克力的魔法也击中了维亚纳和鲁。食物烘烤器上余烬未熄,混着薰衣草和百里香的芬芳覆盖着他们。花园里,他的头顶上,天空呈紫黑色,犹如他那双眼睛。能看见宽阔的银河犹如一条道路,环绕着全世界。她知道,这可能是唯一属于他们俩的时间,可这个念头只不过隐约让她沮丧。正相反,一种逐渐强烈起来的对现实、对完美的感受充实了她的内心,压倒了她心里的孤独。这算不算“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最完满的注解?
维亚纳还是走了。依旧唱着那支神秘的歌谣,被二月里的风卷携而去。她的腹中孕育着新的生命,那是鲁带给她的爱的礼物;身后,她留下的巧克力店自然会有人再开下去——至少,如今充塞着镇上每一个角落的欢乐是再也没有什么人、什么势力能夺走了。
其实没有人逼她走。雷诺神父早已全线溃败,他身上那个处处完美却僵死的神终于蜕变成了缺陷重重但鲜活的人。还有鲁,只要想一想他那忧郁而留恋的眼神……可是苦苦地逼着维亚纳离去的人正是她自己啊!她生来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短暂的停留只是下一次出走的前奏。在她的血管里,奔涌着善良、激情、聪慧,而更多的,是自由。
我依稀看到了卡门的影子,还有萨拉,那个古怪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曾经,这样的小说让我莫名惶惑,胸口总是被怅然若失的情绪塞得满满的,不晓得该怎么解脱。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每个女人心里都藏着出走的梦,挣脱羁绊的念头是那样强烈又那样执拗地与内疚同在——问题是,又有几个女人坦诚勇敢如维亚纳,会义无返顾地直面它,一次次地把流浪之梦化为现实?
据说《情迷巧克力》的灵感来自作者乔安·哈瑞斯本人的家,她自己就出生在一个糖果店里。她的曾祖母曾被当地人视为女巫,会用巫术治病,像维亚纳一样,看透世人深深浅浅的隐衷。
我想,这个故事一定在哈瑞斯心里藏了很久。她让岁月打磨它,凭梦想感悟它……终于有一天,这故事的空间变得很大很大,她心里怎么也装不下了,便从笔尖汩汩地流淌出来。
阿甘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
维亚纳说,幸福,要么像一杯巧克力那么简单,要么像人心那么曲折,那么苦涩,那么甘甜,那么鲜活。
所以,为了读懂生活,参透幸福,让我们好歹给自己留一点甜蜜的特权,尝尝巧克力吧。
------------
当年拼却醉颜红(1)
------------
——梦露拾遗
题解:语出宋人晏几道一阕《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爱其辞藻缠绵而不失犀利,然既无切肤之感,其意终不甚解。近日遵嘱草成此文,惟欠提神醒目之题眼。恰闲读床头常备之《宋词小札》,乃重温佳句,始悟其道尽人世玄机、红颜沧桑,遂窃之以冠拙文,竟甚合。是为之记。
被拍卖的梦露
时间:1999年10月27日至28日
地点:纽约,Christie(有译作“佳士德”的)拍卖行,洛克菲勒中心
事由:玛丽莲·梦露私人物品现场拍卖会,批号9216
当日的盛况据说空前绝后,有目击者妙笔生花,“大堂内华灯熠熠,室外亦为之生辉,仿佛从大门里溢出来的,是白昼……橱窗内,透明的人体模型上,大大小小的银盒子里,都能觅到玛丽莲·梦露的芳踪遗迹……”看了这样的报道,眼里顿时目迷无色,耳边则是一片环佩玎当之声,煞是热闹。
美国最重要的电影频道AMC,拿到了拍卖会的独家直播权,领衔主播的是台里挂头牌的主持人约翰·伯克。Christie的官方网站上也有全程直播,点一点鼠标便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梦露曾拥有过的一切。
在此之前,415页、售价85美元的拍卖目录先行出版,短短一个月就卖掉了28,000册;而梦露的遗物在堆上拍卖台之前,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洛杉矶、伦敦、巴黎、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转了一大圈,参观人数超过75,000。Christie一向是以推介高档美术作品着称于世的,此番拿出了对付达芬奇、毕加索的排场来作梦露的秀,一样沸反盈天,捧场客络绎不绝。27日当晚,主会场里坐了1,000位阔佬,另有500名auction-goer(这个词不太好译,大略是“拍卖会常客”的意思)挤在分会场里。场内开通了100多条电话线——平日的两倍——接受热线投标。
Christie主管市场推广的副总裁、本次拍卖会的主办人南希·瓦伦蒂诺踌躇满志,“我们很激动,因为通过拍卖梦露的私人物品,可以向公众及拥趸展示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果真如此吗?
拍卖会上最弹眼落睛的,还是那些珠光宝气的货色。一款大鞋商塞尔瓦托·弗拉戈莫制作、表面镶有莱茵石的红缎鞋,估价4,000-6,000美元,喊到48,300元才落槌。买走这双鞋的,居然是塞尔瓦托的儿子马西莫,想来他是要重祭老子的金字招牌,借着梦露的一缕香魂,作镇店之宝了。
无独有偶,设计师托米·希尔费格也一掷千金,买下了梦露在《没有弯道的河流》中穿过的三条牛仔裤($42,550)和她在最后一部电影《不合时宜的人》(与克拉克·盖博合作)里穿过的皮质牛仔靴($85,000)。据称,他将把这些戏服用镜框包装起来,悬挂在寓所里。
一件棕色几何图案、腰间配带的手织羊毛衫——梦露在1962年曾穿着它在加州圣·莫尼克海滩留下一套玉照,摄影师是大名鼎鼎的乔治·巴里斯——以52,900美元成交(是估价的10倍!);至于当年梦露在电影《让我们相爱》中身上的那款三角背心系带(原文是halter-neck,很形象、很简洁,只可惜译过来就没这个味道了)礼服,即便穿在冷冰冰的人体模型身上,依然能摇曳出万种风情来,价格一路飚升到167,500美元。略知一些背景的,或许会想到这部片子是梦露与法国小生伊夫·蒙当唯一的合作结晶。据说梦露的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一看到两人四目相对的神情,便心知不妙,干脆扬长而去,眼不见为净。
这段情当年也算是如火如荼。烈焰燃尽,米勒与梦露黯然分手,蒙当却回到了西蒙·西涅莱的身边——西涅莱是拿过奥斯卡的大明星,面对咄咄逼人的梦露,始终不疾不徐,一派大家风度。“如果梦露爱上我丈夫,那说明她有很好的鉴赏力……”
在梦露“鉴赏”的名单上,自然还有她的第二任丈夫、棒球明星乔·迪马·乔。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9个月,留下的唯一证物或许就是那枚嵌了三十五颗钻石的白金婚戒。拍卖现场,婚戒最终归属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买家——虽则花了772,500美元,到底可以换来跟梦露“再续鸳梦”的机缘,即便只是假想,也不无满足感了。
也有很煽情的段落。21号拍品是一架白色的钢琴,尺寸很小,是梦露儿时母亲送给她的礼物。钢琴一度转卖他人,直到梦露成名后有了闲钱,花了好一番心思,才用高价辗转买回来。而今,钢琴,加上琴凳,连同一个忧伤的故事,换来了772,500美元,买家同样没留下姓名。
梦露的几本藏书静静地躺在花团锦簇中:《包法利夫人》、《太阳照常升起》、《秋日》,甚至还有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你完全有理由怀疑这纯粹是“性感尤物”附庸风雅的道具。——就像当年《王子和歌女》(男主角是劳伦斯·奥立弗)的首映式上,梦露嗲声嗲气地宣称自己最想演的是《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格鲁申卡,话音刚落,马上就有记者接口,请她把“格鲁申卡”拼写出来。
梦露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头脑——这几乎已经成了一条真理。或者可以这样说,世人给了她空前绝后的鼓噪着激情与欲望的掌声,她便没有权利再指望得到尊重——尽管她嫁给了写《推销员之死》的阿瑟·米勒,尽管与她演对手戏的是演惯了莎剧的劳伦斯·奥立弗,尽管她拿过一届金球奖的“最受欢迎女演员”,尽管她去听过契诃夫的侄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同事迈克尔·契诃夫讲课,尽管她或许真的能看懂《都柏林人》,照样于事无补。人们只记得那个赤身裸体躺在天鹅绒上拍月历招片的梦露;那个宣称自己睡觉时只穿“香奈尔五号”的梦露(事实上,不管穿什么,患有严重失眠症的梦露一向很难入梦,即便服双倍剂量的安眠药也无济于事);那个在招待会上细肩带断开(据说断得恰到好处,timing掌握得炉火纯青)的梦露;或者是那个拍《七年之痒》时在曼哈顿东六十一街的地铁通气口上、让铁栅盖下的特大鼓风机吹起白色长裙的梦露。
------------
当年拼却醉颜红(2)
------------
那场戏是在1955年的某个清晨拍的,当时街上站的旁观者竟有千人之众。当年盛景,简直就是一场集体意yin。
以小人之心揣度,时隔45年以后的这次拍卖会,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场集体意yin,只不过规模更庞大、名目更堂皇罢了。
意yin的高潮,是55号拍品的登场:一俟宣告,主会场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中,紧接着,柔和的灯光徐徐亮起,勾勒出一件缀满宝石的紧身礼服,耳边同时回荡起梦露唱的生日歌(平均唱一句歌词,大约喘气三次),室内掌声如潮。1962年,梦露确实曾穿着它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唱过生日歌——“HappybirthdaytoJohnKenndy(约翰·肯尼迪)”。
拍下这件礼服的,是一家名叫“莱普利之‘信不信由你’”(Ripley’sBelieveitorNot)的纪念品商店。信不信由你,老板花了1,267,500美元买下这件旧衣服,依然笑得合不拢嘴,一迭连声地夸耀这是一桩好买卖。这个天价同时创下了世界女装拍卖史的新高峰——在此之前,最高记录是由戴安娜的一款蓝色天鹅绒礼服保持的,成交价222,500英镑。
拍卖会最终以筹得13,405,785美元圆满收场。面对此景,拍卖会的座上客、当年与梦露合演过电影的托尼·科蒂斯好不感慨,站起身说,“梦露如果身临其境,一定会激动万分,因为至今还有那么多人热爱着她。”
说这话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忘记,当年他曾以怎样不屑的口气,说过一句更惊世骇俗的话——“吻梦露的感觉,就像吻希特勒!”对此,梦露当时的反应是:“问题一定出在他身上。”
在总共576件拍品中,也有那么一些琐碎到几乎不值一提的东西:塑料杯,蜡烛,普列克斯玻璃制成的卷筒纸盖,就连宠物狗的标牌和执照(狗是名歌星弗兰克·辛纳特拉送的),最后也以63,000美元成交。而其中最不起眼也最触目惊心的,或许是那张小纸片,上面有梦露用铅笔草草写下的几个字:他不爱我。
原来,“至今还有那么多人热爱”的梦露也会为了“他不爱我”而耿耿于怀。或者,这就是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被写”的梦露
这样的题目很日本化,让人联想起三浦友和的回忆录《被写体》(卖点当然是百惠)。梦露没有山口百惠的好福气,有生之年未曾读到过别人(哪怕是爱人)厚道、公正的评价,香消玉殒以后倒是不断地“被写”,成了出版商取之不竭的财源。
可以很确凿地说,至少在娱乐行业里,关于梦露的传记,其数量之众,无人能出其右。单单是用英语写的,就有七百余种,而且这个数字还以每年十几种的速度递增。即便要在这七百多种里选择某种标准大体分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早年,剧作家本·海切曾以梦露自述的口吻,写过一本题为《我的故事》的回忆录,用哀婉得略嫌过火的姿态,把梦露还原成了诺玛·琼(原名)。琼的童年没有父亲,那个与她母亲格拉迪丝私通的莫坦逊驾机器脚踏车丧生的时候,梦露还没从娘胎里出来。琼甚至一度住过孤儿院,据说她在那里就曾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早期症状,大叫“我不是孤儿!”身为电影剪接员的女儿,大银幕寄托了琼所有的梦想,她喜欢琴逑·罗杰斯的歌舞片,也迷恋克劳黛·考尔白在《罗宫春色》中泡的牛奶浴。当然,《我的故事》里也提到了那架白色的钢琴。
此类相对比较善意的传记,还包括专栏作家西德尼·斯可尔斯基和诗人诺曼·罗斯特恩的作品,他们都是梦露生前的好朋友。
凑这份热闹的,自然也少不了她的亲人。梦露同母异父的妹妹柏妮丝写过《我的姐姐玛丽莲》,而她的第一任丈夫更是当仁不让,他写的回忆录,标题就值得玩味:《玛丽莲·梦露的私密的快乐》。
何谓“私密的快乐”?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不好妄作评断。关于梦露的第一段婚姻,向来就有很多版本。一说类似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梦露的少女时代,因其母长期患病住院,一直住在保护人格丽丝家。格丽丝的丈夫心怀不轨,被太太察觉,于是格丽丝痛下决心,托人介绍了邻居家的儿子,草草地把祸水泼将出去;另一种说法要浪漫得多,说梦露读中学时结识了一个大学生,一见倾心,喜结良缘。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梦露第一次做新娘,年仅十六岁,新郎名叫詹姆斯·多尔蒂,大体还算得上是良材美质。四年以后,梦露开始当模特,两人的分歧愈来愈不可调和,结局自然是劳燕分飞。
彼时的梦露,无论是披上婚纱,还是脱下婚戒,都只是她自己的事——没有人费心去数她的戒指上究竟有没有嵌过钻石,或者嵌了几颗钻石;彼时的梦露,未必想过会有一夕成名、艳惊四座的际遇——拼却红颜,赢得的是无双的荣华,输掉的却是“私密的快乐”。
及至与乔·迪马·乔联姻,梦露就再也无权享受第一次结婚时的那份清静了。英国出版社ThamesandHudson在97年11月出版了一本《完整的玛丽莲·梦露》,用词条的形式把有关梦露的信息、资料重新整合,事无巨细,洋洋大观。其中就能找到一个名为“梦露与乔的蜜月”的条目:
新人先在加州帕索罗布尔斯的一家名为“克利夫顿”的汽车旅馆里共度良宵(期间曾在温泉旅馆的餐厅里用餐,也有人说他们这顿饭是在“克利夫顿”吃的)。翌日,乔携同梦露,驾着他那辆深蓝色凯迪拉克直奔棕榈泉附近的一座山间小屋——小屋是梦露的律师洛埃德·莱特借给他们的。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两周的光阴,对他们而言,实在不啻为一种uncommonluxury(不同寻常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