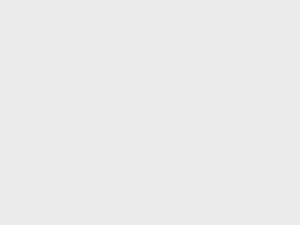- A+
引子
公元一九九八年仲夏的一个下午。与已经流逝但仍存在于记忆当中的七千多个日日夜夜相似,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标记的日子。我站在一座陌生城市的一所三流旅馆的楼顶上。下午四点钟的阳光丰盈的让人目眩,我喜欢这种被温暖而不是炎热所环抱着的感觉。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疯子般的车流恍如另一个世界。"这一切与我无关",心里很自然的就有了这样的怪异想法。而在阳光的浸润下,我觉得自己开始变得轻飘飘的,像是一粒尘埃般浮在了空中,阳光就这样从我的五脏六腑中缓缓穿过,让我看见了躯体中的那些阴霾和肮脏。"这是幻觉吗?"我问自己,心里有了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又在刹那间倏尔远逝。我只在隐隐中感到我站在这座楼顶上是一次机缘,在我的一生中注定会有这么一天,让我从此开始发现些什么自己原本就有但从未意识到的东西。
就这样,从那个五月的下午开始,我开始找回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一)
汽车已经开始发动。车下原本就嘈杂不堪的人群更加乱成了一片,密集的手臂开始参差不齐的挥舞起来,许多人的嘴巴大张着,显然都是在喊叫着什么。我的脑海中突然间一片空白,虽然我知道人群中的手臂有为我而挥动的,叫喊也有对我而来的,但是我却无法看清眼前那些原本异常感人的细节,听不清任何叫喊。也许我是试图将这一切全部记住。然而我却恰恰遗漏了所有的细节而成了一个旁观者。一个在观看一部黑白无声片的旁观者。
汽车终于启动了。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种全部场景都值得记忆但是你又无法清晰记住其中任何一个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正在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女生冲向了我所在的车窗,仰者的脸上满是泪痕,她大声喊道:"我是爱你的"。我象是被重击了一下似的,有些愕然,"是对我说吗?"我自问,"如果不是对我,我却又分明听的真切。"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这些,汽车已经驶出了校门,我赶紧扭头去看那人到底是谁,但我只能看见一个蓝色的孤独身影,站在已经远离送别人群人的地方,并且离我越来越远……
那是一件淡兰色的长裙。
无声影片仿佛在此定格。从那时起我好象就失去了记忆,对已经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而那张满是泪痕的脸却成了一个特写,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于是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总是忍不住问自己:"她到底是谁呢?"。日子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反正又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洗刷,我真的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我所能记起的这些,是发生在公元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的上午,那是毕业离校的日子。
其实这一切才是我最该忘记的。因为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它成了我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
一九九五年八月的一天,我站在了一座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这里距离我曾经生活过近二十年的那所小镇有两千公里之遥,这种距离感只有连续乘坐过四十八小时硬座火车的人才会有一个深切的感性认识,这意味着我只能也只愿意每年的春节时才回家。在这里我只有住处而没有家……
这所城市在每晚十点钟以前是一锅烧开了的粥,并且是那种已经不知熬过多少次的老粥,令人望而生畏。而我每天必须要做的就是在这锅热气腾腾、乱乱哄哄的老粥里奔行与单位与住所之间。每当我骑着单车穿梭饶行于车流、人流和各式摊点之间时,我总觉得自己象是电脑游戏中的小精灵,一不小心就会被任何一个陷阱所吞没,然后我的人生履历上会被大大地打上这样一行字母:GAME IS OVER!我好象一直有这种预感。
可是这样的一天到目前为止尚未到来,游戏仍在进行当中,于是我仍得以尽情表演。当然玩家是世界,不是我。工作象我所学的专业一样索然无味,我是实实在在把它当作了我的谋生手段,它对我来说毫无乐趣可言。真正属于我的时间是在下班以后,而这些时间又大多被那些我已记不清的往事占据着。我所能记清的那些,大部分都成了隔夜的啤酒——只剩下马尿味了。只有那张微微向上仰起、且满是泪痕的面孔还一直是个谜。她到底是谁呢?
(二)
在日复一日的样板生活中,我开始感到了令人颤栗的孤独。尽管我早有了思想准备去面对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但这一次我发现一个人的想象力无论多么丰富,都难以与活生生的现实相匹敌。在这个崇尚自我感觉的世界里,孤独是一种让人羞于启齿的通病,只要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孤独,就仿佛是将自己当众剥光了衣服一般让人无地自容。于是每个人都咬着牙硬撑着,于是大家都有了讳疾忌医的嫌疑。当然我也没有当众剥光自己衣服的勇气,我选择了将自己的孤独涂抹在纸上,或是在日记中,或是在写给蝎子和教徒的信件中。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人生有很多事的归宿只有两处:心或者坟墓。我早已记不清这是哪位名人说的了,然而我却深信不疑。
我想对于我来说,那些怪异不堪的想法也只能归宿于这两个地方。
蝎子与教徒是我肯将自己的孤独展现给他们的两个人。蝎子是一个有着张娃娃脸的小伙子,这张娃娃脸总使他显得稚气未脱,也常是我调侃取笑他的原材料之一;而教徒则是位气质不俗的而又天真烂漫的女大学生。我们三人实际上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只是因为所上的大学不同才天各一方。我与蝎子因为上得是大专,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上班了,而教徒却还在一所重点大学里继续"修炼"。
我有时很奇怪自己能同时与蝎子和教徒两人保持那种无间的友情,因为他们迥然不同的生存态度与方式使得原本"两小无猜"的两个人竟然无话可说,甚至相互不以为然起来。我是从蝎子那里知道他们小时侯就经常在一起玩的,教徒却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些。在蝎子眼中,教徒可能是属于"虚伪"的那个圈子,而在教徒眼中,蝎子也许属于"堕落"的圈子。其实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这样相互评价过对方,但我感觉我的猜测是对的。这样以来,我的处境就不免尴尬,但使我奇怪的是我竟然与他们相处的无懈可击,这让我很是欣慰和得意,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我不愿失去的朋友。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一座花园,它们或是生机勃勃,或是荒芜不堪,但是却都有其独到之美——只要你用心去理解它们。在与蝎子和教徒相处的过程中,我慢慢明白了这个道理。
蝎子是一个极不安于现状的家伙,但在经历过许多次的挫折后,他变得多少有些玩世不恭起来。而这也正是我所欣赏的。他现在正蛰居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个小站的防沙工程队,确保着我们国家第一条高原电气化铁路的畅通。这听起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且在他写给我的信中也总是将自己的生存状态描述的漫不经心,并不时用一些调侃和黑色幽默来使原本孤独、空虚、迷茫的生活显得生动一些。但是我知道事实上他内心深处隐匿着巨大的忧伤。于是我总是些写"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经一番锤炼,怎成一段锋芒"之类让我面红耳赤且深感虚伪的语句给他。这一切连我自己都已经不再相信,但除此之外我仿佛别无选择。
教徒的来信却更象一杯白水,没有那么多的嘲讽与抱怨。她时常会在信中大段地描写晴朗的星空或是秋雨绵绵的日子,以及一些根本让我笑不出来的校园趣事。也许是因为我未曾有过这样的记忆,而她的来信又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所以我也就耐着性子不厌其烦地读着。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开始对她那种纤尘不染的精神世界艳羡不已,甚至有几分嫉妒。我好象不曾有过这样的时光,生活很早就教会了我忧郁和不安。我也早就变成了一个俗不可耐且无药可救的家伙。
尽管对教徒那种超然物外的生存态度羡慕不已,但是我心里很清楚,那样一种柔弱的世界在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要知道面对这个纷乱不已的世界,想坚守住内心的那份平和与沉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日渐枯萎而无能为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学会在浮躁和麻木中生存。人好象都有这样一种嗜好:当自己明白在什么情况下"1+1"不等于2时,总是喜欢先考考别人,然后在玩味够别人迷惑不解的神情后,再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们。我也不幸染上了这种癖好,于是就常在给教徒的信中向她灌输那些连我也尚未能运用熟练的"社会经验",并乐此而不疲。其实我并不是想改变她的世界,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徒劳的——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就索性让他睡个够,他总有醒来的时候。如果贸然去惊醒别人的美梦,岂不是有"大煞风景"的嫌疑吗?
我更喜欢看着别人慢慢醒来。就象我一样。
(三)
然而清醒着是一种痛苦的存在状态。我在白天毫无知觉地充当着社会机器的螺丝钉,而在暗夜,则无时不刻都在体会着那痛入骨髓的迷茫和失落。我开始不停地问自己那个愚蠢的问题:我到底为何而存在?小时候是为了长大,长大了就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了;上学后是为了考学,考上学就可以有一个好的未来了。等到工作以后,发现自己突然间就没有了目标,或者说目标就变得模糊起来。谁也无法说清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娶什么样的老婆,住什么样的房子,生什么样的孩子,甚至死于什么样的疾病或是天灾人祸……看来人生就是这么偶然与无常。人们常说年少无忧,那是因为年少时意识不到这些。"我思故我在",思则痛苦。于是"我在故我苦"。
蝎子有些时间没有来信了,不知道又醉卧于哪片胡杨林下。到是教徒的信还是那么规律地每周一封,从不间断。而我也终于有点事做了————单位派我去出差。这可是一件好事,总比闷死在办公室里强,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囊(特意带了一打邮票和信封),便欣然上路了。火车在夜幕中寂寞地穿行。而我却难以入睡,自从上班以后,我就不幸染上了失眠的"爱好"。车窗外的城市与村舍一座又一座地被抛向身后,当火车在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开始进站的时候,我无意中向车窗外看了一眼,站牌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c城"。我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许多我费劲心机也想不起来的往事一下子就涌了出来。c城,这不是林子的家乡吗?我好象是费劲周折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顿时浑身无力地跌坐在了座位上。
c城,我曾经魂牵梦萦的城市啊!我雨中的c城,我雪中的c城,我阳春三月的c城,我血色黄昏的c城,我听林子描绘过无数次的c城;我在心里也向往过无数次的c城。如果不是那一次的谎言,也许我就将在这里生活的c城,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林子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嬉戏,在这里成长,城市的每一条小巷都有她纤小的足印;每一条小河都映射有她亮丽的身影;每一缕清风都亲吻过她乌黑的长发;每一盏街灯都照亮过她的青春的面颊。林子深爱着的c城,我曾经深爱过的c城。林子的c城。
火车缓缓启动了。我面对着c城泪流满面,不是为了这一次的错过,该错过的我早就错过了,而是为我终于找到了我青春的开头。我那一去不返的青春的开头。林子第一次离开c城是在1992年的9月,前往北方a城那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我们相遇在那个陌生的城市的火车站。
找回的第一段记忆也应该是在a城的火车站。
(四)
经过将近50个小时的颠簸,火车终于到达了我的目的地。由于火车晚点的原因,当我灰头灰脸地站在A城车站出站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半多了。乍见站前广场上的一片霓虹竟然使我有些目眩,我长出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开始去找入学通知书上说的能直达那所大学16路公交车。谁知这个广场上连个指示牌也没有,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放下沉甸甸的背包,向四周巡视了一圈,想找个人问问。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按年龄划分,你通常最容易从两种人那里得到帮助,一是老年人,二是青年人。中年上下的人常常回对你的发问很不耐烦————-这也许与他们每日忙于应付生计有关吧。
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东张西望的,好象是在等人。我径直走过去,轻声问到:"您好,请问16路汽车站怎么走?"女孩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去B大学报到的新生吧?",我点头默许。她笑了一下,用手指着广场右边的一座高楼说:"就在这座楼后面,绕过去就可以看见"。"谢谢",我道谢后拔腿就要走,"等一下",女孩叫道,我便停下来等她说话,"是这样的,我也是去报到,本来说好有人来接我的,可能出了什么差错,我一直都没有等到,再等下去我恐怕连末班车也要错过了,您能帮忙带我一起走吗?"女孩用殷切的目光看着我说,"这有什么,一起走吧",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那就太谢谢您了"女孩显然非常高兴,一双并不大的眼睛泛着愉悦而柔和的光,"我还有几件行李在那边,我们一起去拿一下吧"。我点了点头便跟着她向车站的另一边走去。
几分钟后,我就为我轻率的应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竟然携带着一个箱子外加两个旅行包,最要命的是,那个并不算大的箱子竟然象装满了铁器一样沉重。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在她的帮助下战战兢兢地将箱子扛上了肩头,而且没走多远肩膀就开始火辣辣的痛。我在心里暗自嘀咕:"这个小丫头可真够精明的,我这路可算没白问!"女孩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艰辛,提议歇一会再走,我本想顺水推舟,可恶的虚荣心这时却砰砰的律动了几下——-我从几乎已经有些变形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没事,走吧"。女孩没有再说话,看得出来她手里那两个包也不轻。
于是一路无话。
我发誓我一生中都没有感觉过再比那150米更长的路程了。当我们登上公交车的时候,我的半边肩膀就象是被卸掉了一样,完全失去了知觉。我瘫坐在座位上,呼呼地喘着粗气。"真不好意思,我的箱子太沉了",女孩一边将一张纸巾递给我一边说道,我擦了擦脸上的汗,问她"装的什么宝贝,这么重?",女孩诡异的笑了笑没有回答。
末班公交车终于吭吭哧哧地启动了。我们向学校驶去。
(五)
直到现在我依然对在1995年9月的那个夜晚在校门口接待站值班的师兄们心怀感激。是他们用三轮车将那个差点将我累吐血的箱子拉到了女生公寓,我才得以幸免于难。当她先办完手续离开的时候,我还在接待站办一些手续,所以根本没有时间说些什么,她便匆匆坐上三轮走了。我收拾好一摞表格正准备离开时,她却从前面一栋楼的拐角处跑了回来,将一块用一条手帕包着的冰砖交给了我说:"把这个敷在肩膀上会好一些",我说了声谢谢,便接了过来,她又说:"对了,忘了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系的?""丁凡,土木系"我一边用冰砖敷着肩膀一边回答。正在这时,眼前人影一晃,她又跑着去追三轮了,"再见"的声音传来时,她已经快消失在楼的拐角处了。"真是够神的"我自言自语道,用左手按着冰砖顺着接待处的人告诉我的方向去找2号男生公寓。
男生公寓近多了,没几步路就到了。宿舍里只有两个人来了,而且都在蒙头大睡,我很快领来被褥床单,简单洗漱了一下就把自己放倒在了床上。虽然经过冰敷肩膀好多了,但还在隐隐作疼,我在脑海里回忆了一下整件事,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忘了问那个女孩的姓名,而且她的面容在我的记忆中也是模模糊糊的,只有那双不大但却很有神的眼睛显得清晰一些,在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她到底长什么样之前,我就如死一般的睡着了。
就是在那样一个九月的夏夜,我在做了一件好人好事的同时踏进了B大的校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是从军训开始的。那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象木头桩子一样立在炎炎烈日下练习队列。每次教官开恩说"解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就地坐卧成一片。到了后来,又开始踏着军乐踢正步,那军乐以异常雄壮的节奏刺激你的运动神经,让你情不自禁地就想去合拍。结果大家都落下了病根——-第二年新生入学军训,校园里再次回荡起这个乐曲的时候,我们宿舍的8个人有6个人说头痛,当然也包括我了。
到了九月底的时候,军训大阅兵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学校武装部的部长用辆破卡车拉着我们到处去向军队借军械,学校餐厅的二楼被腾出来作为军械库,里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轻重枪械。为了保证方队能在阅兵中取得好成绩,教官开始剔除个别实在不可造之才。说来惭愧,我很荣幸地与一个踢正步时总是顺拐的家伙一起被优化了下来。我心中窃喜:"这下子可解脱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回去睡大觉,白天我们两人用一辆小三轮给兄弟们送几趟水,然后坐在树阴下看他们受苦,看到谁被教官训斥时,再扭过脸窃笑几声。到了晚上,我们就去军械库值班,负责收回各个方队的枪械,并在大枪小炮中睡一觉,如此而已。
就这样,入学第一个月我就尝到了落后的甜头。
(六)
大阅兵的那天,学校的大操场上着实热闹了一番。我躲在主席台侧的一间小房里放录音,就是在方队模拟演习的的时候,将预先准备好的警报声、高射机枪声、迫击炮声、60火箭筒声一一播放,以营造演习气氛。当我斜着眼透过小房的窗户看见一个个整齐的放队行着注目礼通过主席台的时候,我体会了一把作将军的心情。可惜我无法以标准的军姿(我好像也一直没能练成,要不然教官也不会总给我开小灶了)向他们还礼,要不然我可就过足瘾了。
可惜好日子在阅兵后就结束了,我和"顺拐老兄"又重新回到了宿舍,很快我们就开始了"三点一线"的大学生活。
我一直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人们将大学校园称之为"象牙塔",是塔没错——-大家都削尖了脑袋,想尽一切办法往里头爬,爬得越高身价也就越高。可干吗非是象牙的呢?在我看来大学就是个大染缸————没色的给你上点色,有色的给你镀层金。于是乎摇身一变,大家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也许我天生就是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反正没有多久我就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中学老师对大学生活的描述是谎言————或许他们那个年代大学是另外一个样子;父亲母亲对大学的厚望是虚妄————他们要指望这里能将他们的儿子培养成他们心目中光宗耀祖之辈恐怕要大失所望了;我对大学的憧憬是个毫无根据的推理————因为大家都趋之若骛,所以一定是个好地方。于是我成了参与这场骗局的唯一一个受害者。老师因为升学率而升任校长,父母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而我却不得不在这里独自应付这场尚未结束的骗局。每当我看见那个头发已经快要掉光的老副教授颤颤巍巍地拿着已然发黄的教案纸向黑板上抄讲义的时候;每当我看见考试后、补考前学校后院(教职工生活区)一派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的时候;每当我看见所谓的天之娇子将一支手电筒吊起来,通宵达旦"修长城"的时候,每当我看见身边那为了填补各自的空虚而进行的一幕幕感情游戏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切肤的悲哀————我们十几载的苦读,就为了这些?!我有深深的失望,却无法直言。
当人们遭遇失望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在失望中挣扎,去寻找下一次的失望,另一种则是在失望中消沉,只失望这一次。
我选择了后者。
于是我的大学生活就注定了要在消沉和绝望中渡过。
(七)
人的记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旦找到了那把开启库房的钥匙,所有的往事都在刹那间如潮水一般涌出记忆的闸门。这一次C城的不期而遇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忽然间我就找回了那段丢失了的记忆,所有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在我的脑海里纤毫毕现。然而我却非常肯定那个穿淡蓝色长裙的女孩并不是林子,我好象根本就不认识她,只是隐约感觉有几分似曾相识。她究竟是谁呢?在纷乱的思绪中我还是无法想起。
当对大学生活彻底失望以后,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说我完全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其实一个人由里到外完全转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只是换了一种活法而已。人就象是水,有时以云的方式存在,有时以雨的方式存在,还有时以冰的方式存在,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存在,只不过它们都是水而已。以水这种形式存在着的人也可以轻易地用一个比喻来定义他存在的状态及过程:用你洗衣服甚至洗尿布,你就是变成了脏水、臭水;在大旱天用你浇庄稼,你就是成了"贵如油"的东西;你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可以任人遨游,也可以溺毙他们;在杯中是圆的,在池中是方的……总之,就是这样既重要又不重要;既有个性又无个性;既是伏天甘露又是洪水猛兽地存在着。我总觉得冥冥中有种力量在替我们安排着一切,我们都无法摆脱这种安排。对于我来说,1992年的12月31日发生的事,就是一个神奇的偶然。
那天晚上,班级组织了入学后的第一次联欢会。无非是先集体打了顿牙祭,然后聚集在教室里搞些无聊的游戏。我实在感到索然无味,就偷偷开溜了。我上了二楼的机械系,将郑平叫了出来。他也正被乏味的游戏搞得哈欠连天,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去西门外得小酒馆喝酒。于是蹬上我刚从旧货市场买来不久的那辆旧自行车直奔西门外。郑平是我在军训时结识的机械系的新生,他来自南方沿海的一所小城,但却全然没有南人的那种阴柔之气,而是非常豁达的一个人。郑平的脸型属于轮廓分明的那种,浓眉大眼,嘴唇略微偏厚,一看就给人一种坚毅、倔强的感觉。我和他交往了几次,便觉意气相投,而且非常默契,于是很快我们就成了死党,经常在一起瞎混。
小酒馆离学校不远,出了西门就到。我和郑平要了一瓶二锅头,就着一碟盐水花生、一碟松花蛋,就天南地北地闲扯起来。大多是关于中学时的校园逸事和关于老师们的一些笑话,间或还聊些现在各自班级里的一些"神人、神事",谈笑间酒瓶已是空空如也。等老板催我们赶紧回学校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我和郑平都有点晕晕忽忽,他比我还厉害些,我只好用自行车晃晃悠悠地带着他回宿舍。就这样在距离1993年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走向了我一生可能注定要再次邂逅的那个人。